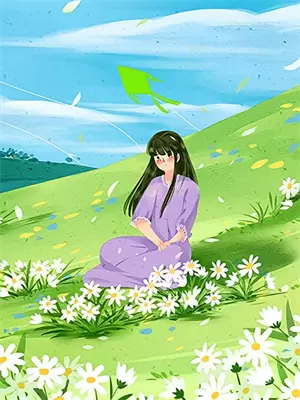- 跨年夜的课剑道日语完本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跨年夜的课(剑道日语)
- 分类: 其它小说
- 作者:乌橘梅子
- 更新:2025-10-22 18:54:52
《跨年夜的课剑道日语完本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跨年夜的课(剑道日语)》精彩片段
元旦跨年夜前的最后一节课,铃声刚过,高三2班的多媒体屏幕还亮着倒计时的残影。
我把印着“大吉大利”的搪瓷保温杯往讲台上一放,杯底与讲台碰撞的闷响,
跟我这一米九的个头倒挺搭——底下学生总偷偷说,看我往讲台前一站,
挡得后排看不见黑板,这会儿估计又在憋笑。哈出的白气裹住讲台边蔫哒哒的绿萝,
我指尖敲了敲黑板,粉笔灰落在深蓝色毛衣上,“别嫌我絮叨,今儿不讲日语语法,
给你们说段我自己的破事儿——保证比模拟题有意思。”那时候我家在吉林镇东头开肉铺,
门口挂着块褪了色的红布帘,一到冬天,帘子里的白汽裹着生肉腥气能飘出半条街。
我爸是街坊眼里的“张一刀”,剔骨刀下去,排骨能剁得当当响,骨渣子溅在铁砧子上,
弹起的声儿都透着利落;我妈总坐在里屋算账,算盘珠子噼啪乱蹦,
那节奏比我后来听日语听力还让人头大。他俩忙得脚不沾地,给我五块钱让我自己买吃的时,
话都顾不上多说两句——“去去去,自己买根烤肠,再买袋辣条,别在这儿碍眼”。
我揣着皱巴巴的五块钱,转头就跟二柱子钻了网吧。那时候我已经长到一米七多,
往网吧沙发里一坐,比老板还显壮,《传奇》里“沙巴克攻城”的喊杀声,
能盖过街对面包子铺的叫卖声。至于成绩?班里四十个人,我稳定在三十八名,
有时候考三十九,还是因为倒数第二的同学请假缺考了。老师批卷时总在我卷子上画满红叉,
像撒了把辣得人眼睛疼的辣椒面,每次叫我去办公室,都得仰着脖子跟我说话,
末了总叹口气:“张云起,你这大块头,咋就不用在学习上?”现在想起来,
真正让我记一辈子的,是小学三年级那次“飞针大侠”事件。
那阵儿我天天蹲在肉铺里的小电视前看武侠剧,觉得李寻欢甩飞刀的样子帅炸了,
尤其是他喝完酒眯着眼甩刀的范儿,我能对着镜子模仿一下午——虽说我人高马大,
模仿起来总显得笨拙,却半点没觉得丢人。有天趁我妈不注意,
我翻出她纳鞋底的粗针——那针比我小拇指还粗,
针尖磨得发亮——学着电视里的姿势往木门上扎,扎得门板上全是小洞,
还跑去找二柱子炫耀“我这‘飞针’比李寻欢的飞刀还准”。结果那天我爸刚从肉铺回来,
满手的油,脱了沾着血渍的黑布鞋就坐在炕沿上揉脚,脚底板上还沾着块没洗干净的肉渣。
我脑子一热,抬手就把针甩了出去——“嗖”的一声,针直接扎进他脚底板,
露在外面的针尾还晃了晃。我爸嗷一嗓子就蹦了起来,疼得直跺脚,
抄起炕边的鸡毛掸子就追着我满院跑。我人高腿长,本能跑得更快,
可看着他一瘸一拐的样子,愣是没敢加速,最后被他堵在柴房里,屁股肿得跟馒头似的,
足足躺了三天,连炕席都被我哭湿了半边。
还是我妈送饭时蹲在门口叹气:“你爸脚底板出血了还惦记着给你留烤肠,你说你这大块头,
咋就这么不让人省心?”大概是那次闯的祸太大,
后来我妈咬着牙凑了五千块钱——那时候的五千块能买半头猪——把我塞进了县重点初中。
她送我去学校那天,反复跟班主任说“麻烦您多费心,这孩子要是再混,您就揍”,
语气里的恳切,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可我那时候没长记性,开学没俩礼拜,
就跟班里几个“兄弟”蹲在二楼栏杆上晃腿。我个子高,往下一看,
正好看见物理老师抱着教案过来。那老师五十多岁,头发总梳得油亮,
苍蝇落在上面都能打滑,风一吹还会飘起来,我们早就怀疑是假发,
还打赌“能不能撑过一阵大风”。我给同桌使了个眼色,
他立马掏出根从家里自行车上拆下来的细铁丝。我仗着个子高,伸手就够到了栏杆外,
趁老师抬头看我们的功夫,轻轻勾住了他头发的边缘——“哗啦”一声,
黑色假发片直接掉在地上,露出里面花白的短发。全班瞬间炸锅,我笑得直拍栏杆,
眼泪都快出来了,没成想老师脸憋得通红,捡起假发片往头上按了半天都没按好,
最后抱着教案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不出所料,当天下午我爸就被请到了学校。办公室里,
物理老师指着我鼻子说“张云起,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没出息!
长大了跟你爸一样剁肉去吧”,他比我矮二十厘米,抬头看我的时候得把脖子仰得老高,
可那眼神像针一样扎人,比我当初扎他脚的那根针还疼。后来每次在走廊碰见,
他都仰着下巴斜眼看我,鼻子里还“切”一声,那模样,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脸烧得慌。
那天从学校回家,我没像往常一样去网吧,而是蹲在肉铺门口看我爸剁肉。
我一米八的个子往那儿一蹲,比旁边的肉案子还高,铁砧子上的五花肉被剁得烂碎,
肉汁溅在我裤子上,我却没躲。看着他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,汗水顺着下巴滴在肉上,
我突然就觉得不服气——凭什么说我没出息?凭什么我长大了就得跟我爸一样剁肉?
可不服气归不服气,那时候快初中毕业了,我课本上的公式像天书,
一元二次方程都解不明白,英语连“hello”都能拼成“helo”,
根本没底气跟人争。最后还是我爸妈托了在教育局工作的远房亲戚,又凑了一万块学费,
把我送进了市重点高中。我爸送我去学校那天,把一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往我肩上一搭,
那包在我手里跟小玩具似的,他只说了一句“最后一次机会,再混,你就真跟我剁肉了”。
我后来才知道,那一万块钱,是他跟肉联厂赊了三个月的肉款才凑出来的。从那以后,
我才算真正收了心。高一选课的时候,我看见“日语”选项,
突然想起肉铺里偶尔来的日本客户——他们指着排骨说“これをください”请给我这个,
我却连一句“好的”都答不上。那时候我就想,要是能学好日语,
说不定能帮家里的肉铺多做点生意,也能让物理老师看看,我这大块头不是只会闯祸。
高中三年,我把网吧会员卡转卖给了别人,每天早上五点就站在阳台背日语单词。
冬天冷得手都握不住笔,我就揣个热水袋焐一会儿再写——我手大,
热水袋在手里跟个小暖炉似的;晚上在肉铺后面的隔间里练听力,隔间小,
我一米九的个子得蜷着腿才能坐下,我妈总端着热牛奶进来,
转身时眼角皱纹里还沾着面粉——她白天在肉铺帮忙,晚上还要做馒头补贴家用,
有时候馒头没卖完,就热两个给我当夜宵。日语成了我最拿手的科目,
每次考试都能考120多分满分150,班主任还开玩笑说“张云起,
你要是把对日语的劲儿分点给数学,说不定能冲一本——你这大块头,要是能考上大学,
以后站在讲台上都镇得住场”。可偏科这事儿,还是没绕过去。我语文能考110多分,
日语稳定在125左右,文综也能拼到180,
唯独数学像块硬骨头——高考前最后一次模考,数学才考了65分,刚过及格线。
我抱着卷子蹲在操场角落哭,个子高蹲下去费劲,膝盖硌得生疼,
日语老师过来拍我肩膀说“别慌,你日语能拉分,把优势科目稳住,
一样能上好大学——你这大块头,要是当老师,肯定能护着学生”。高考那天,
我特意把日语单词本揣在兜里,本子在我大手里显得格外小,进考场前还翻了两页。
最后成绩出来,总分584分——语文112,数学71,日语130,文综271。
这个分数在当年的文科里不算顶尖,
但够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日语系了——那是我早就查好的学校,离老家远,
能让我彻底摆脱“肉铺老板儿子”的标签,而且它的日语专业在全国都有名,
还能接触到外贸、交流生之类的机会。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我爸把肉铺关了半天,
特意去镇上买了只鸡。吃饭时他喝醉了,就跟街坊说“我儿子要去广东学日语了,
以后能跟外国人说话——我儿子一米九的大个子,出去不丢人”。我摸着通知书上的校徽,
突然觉得,那些蜷在小隔间里练听力的晚上、冻得握不住笔却还在背单词的清晨,都值了。
坐三十多小时火车去广东报到那天,我背着塞满日语课本的书包,
书包带在我宽肩膀上显得细细的。路过长江时,
我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——江面上的船像小叶子一样飘着,心里又激动又忐忑,
像只终于飞出笼子的鸟。广外的校园比我想象中还大,可我这一米九的个子走在里面,
还是成了“显眼包”,日语系的迎新会上,系主任一眼就注意到我,
笑着说“咱们专业来了个‘高个子人才’,以后组织活动,搬东西的活儿有指望了”。
也是在迎新会上,系主任说“咱们专业有跟日本熊本大学的交换生名额,想争取的同学,
从大一开始就得好好学,还要有拿得出手的特长”。那天晚上,我在宿舍翻手机,
看见学校社团招新的海报,
其中“剑道社”三个字突然吸引了我——小时候看武侠剧的劲儿又上来了,
觉得握剑的样子特别酷,而且我这大块头,练剑道说不定有优势,还能为交换生名额加分。
我报了剑道社,刚开始练的时候总闹笑话——我手大,握剑姿势总不对,劈砍时力气太足,
竹剑总砸在地上发出巨响,好几次差点撞到社团里的学弟学妹。社长是个大三的学姐,
每次都耐心教我“剑道练的是心劲,不是蛮力,你个子高,重心稳,沉住气才能出好剑”。
我每天放学后都留在社团练剑,手上磨出了茧子就贴创可贴,练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,
就对着镜子调整姿势。大二那年,剑道社要办“中日大学生剑道友谊赛”,
我因为个子高、重心稳,成了主力队员,
跟着学姐去日本熊本大学交流了一周——就是这次交流,
让我摸清了熊本大学的交换生选拔标准:除了日语成绩优异,还要有跨文化交流的经历,
而剑道正好是最好的“敲门砖”。从日本回来后,我更拼了。
日语专业成绩保持在年级前10%,还主动帮剑道社组织活动,写了篇关于剑道的论文,
发表在学校的学术期刊上。大三那年,熊本大学交换生名额下来,
我抱着“试一试”的心态提交了申请,没想到真的选上了——评审老师说,
我这“高个子剑道选手”的形象很有记忆点,对剑道的理解、还有在友谊赛里的表现,
让他们觉得我能做好文化交流的桥梁。拿到交换生通知书那天,我第一时间给我爸打电话,
他在电话里笑得特别大声,说“我就知道我儿子行,以后去了日本,
别忘了给家里肉铺的老客户带点特产——你一米九的个子在日本,肯定没人敢欺负你”。
同类推荐
 反派逆袭系统:掠夺气运宠儿机缘楚风苏浅雪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反派逆袭系统:掠夺气运宠儿机缘楚风苏浅雪
反派逆袭系统:掠夺气运宠儿机缘楚风苏浅雪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反派逆袭系统:掠夺气运宠儿机缘楚风苏浅雪
阿环啊
 身为labubu盲盒首席设计师的我,递交辞呈转岗去前台后,男友干妹妹疯了小雅林晚晚全文在线阅读_身为labubu盲盒首席设计师的我,递交辞呈转岗去前台后,男友干妹妹疯了全集免费阅读
身为labubu盲盒首席设计师的我,递交辞呈转岗去前台后,男友干妹妹疯了小雅林晚晚全文在线阅读_身为labubu盲盒首席设计师的我,递交辞呈转岗去前台后,男友干妹妹疯了全集免费阅读
泡芙圈
 墨韵莹然牧瑶若岚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牧瑶若岚全本免费在线阅读
墨韵莹然牧瑶若岚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牧瑶若岚全本免费在线阅读
竹园VIP
 见君行坐处,一似火烧身赵方芸裴渊完结版小说阅读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见君行坐处,一似火烧身(赵方芸裴渊)
见君行坐处,一似火烧身赵方芸裴渊完结版小说阅读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见君行坐处,一似火烧身(赵方芸裴渊)
易烟
 《墨韵莹然》牧瑶若岚_(墨韵莹然)全集在线阅读
《墨韵莹然》牧瑶若岚_(墨韵莹然)全集在线阅读
竹园VIP
 墨韵莹然(牧瑶若岚)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版小说推荐墨韵莹然(牧瑶若岚)
墨韵莹然(牧瑶若岚)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版小说推荐墨韵莹然(牧瑶若岚)
竹园VIP
 顶流塌房夜,我和死对头互换人生徐若微陆哲免费阅读全文_热门小说大全顶流塌房夜,我和死对头互换人生徐若微陆哲
顶流塌房夜,我和死对头互换人生徐若微陆哲免费阅读全文_热门小说大全顶流塌房夜,我和死对头互换人生徐若微陆哲
浮生长安
 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沈栀沈楠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(沈栀沈楠)
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沈栀沈楠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(沈栀沈楠)
沐澜
 《手撕要逃离原生家庭的养女》中秋宋小蕊_(手撕要逃离原生家庭的养女)全集在线阅读
《手撕要逃离原生家庭的养女》中秋宋小蕊_(手撕要逃离原生家庭的养女)全集在线阅读
折冬痕
 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沈栀沈楠完整版免费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沈栀沈楠
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沈栀沈楠完整版免费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侯府被抄,我带着祖母空投杀疯了沈栀沈楠
沐澜